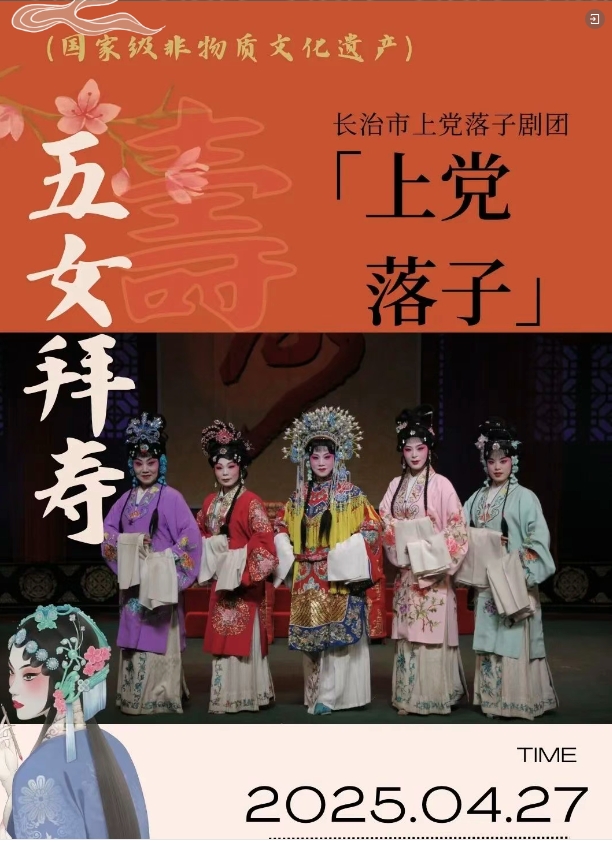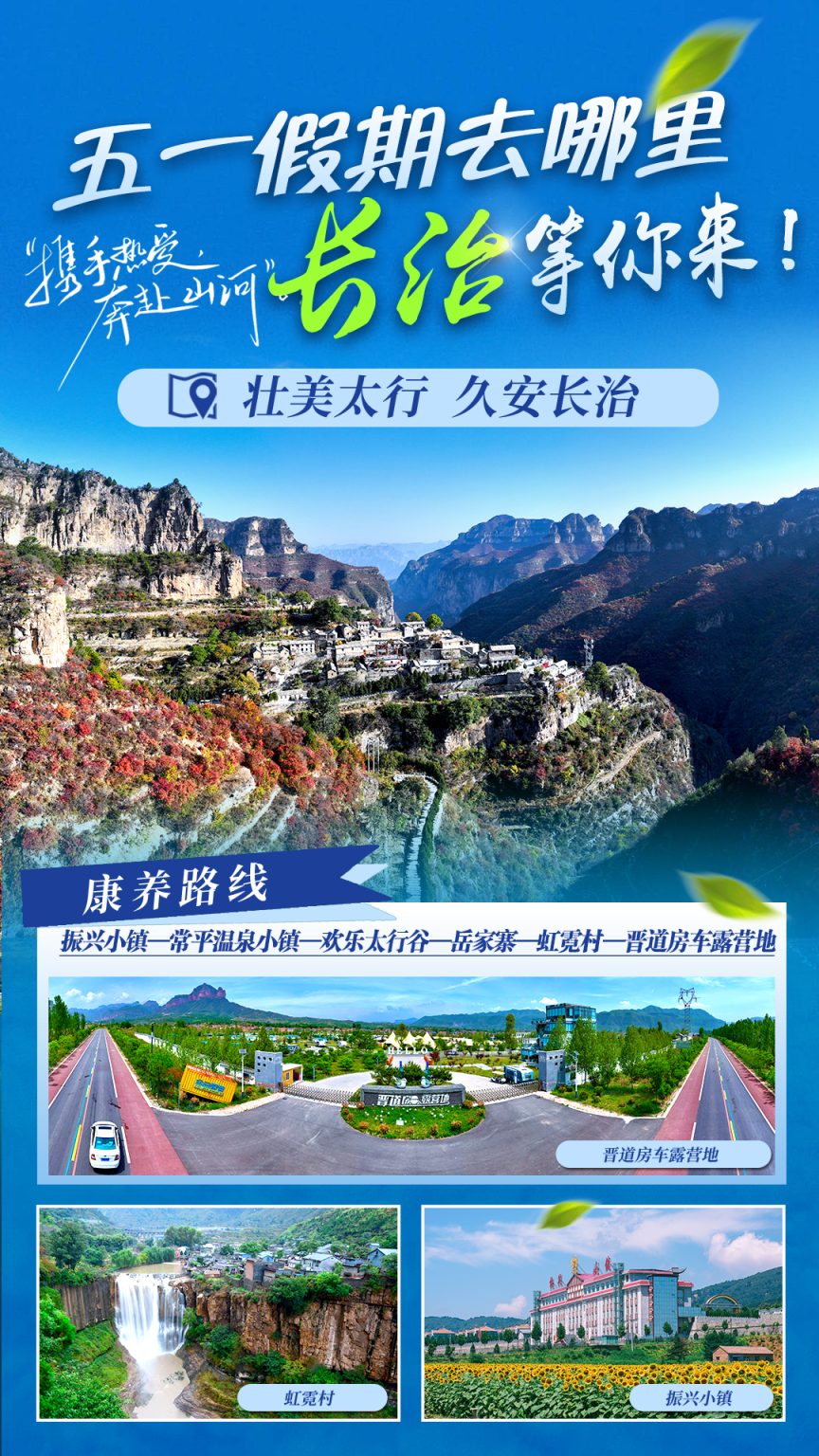乐以忘忧
一
书画印可以说是诗意图像化表达的相对具象性的文化艺术。
艺术家的所谓“天分”,就是擅于运用别具一格的非常感性的形式,神魅地赋能,从而在作品中体现出普通的容易被忽视的物象应该具有的动人灵魂。因此,优秀诗人在书画印艺术表达上往往具有独特的优势。他们能够把浪漫的艺术想象,巧妙地以近似文学拟人、比喻、隐喻、夸张、对仗、排比等语言,巧妙地勾勒、渲染和刻画出含蓄、优美、动人的艺术境界,引发读者身临其境的共情联想,从而实现艺术魅力的感染和共鸣。
李春雨的诗歌就具有很强的艺术张力。如《风过风穴寺》的句子:“七祖塔。檐下的清音/比飞过的鸟鸣更轻,抬高了天空/隐山堂前,小沙弥串起落叶/悬钟阁的钟声推开远山//风过风穴寺/遍地莲花沉寂”。诗虽简短,但言简意赅,其中既有静之动感,又有动中之静;既有马致远《天净沙·秋思》的清简高古,又有哲辨的禅机妙悟,叫人浮想联翩,久久萦怀。
其《在一场孤独里渴望另一场孤独》则颇有柳宗元《江雪》的画境:“一场小雪过后/冬天就挂满枝头,黑与白//白的更白。/旷野,略带寒意/远山孤独//一溪泉水流了过来//要能在雪里隐姓埋名/多好!”诗意清寂,纯洁,淡然,亘古……这叫我想起陶渊明的桃花源,想到林逋的梅妻鹤子,想到意蕴寥廓、悲悯深沉的文人世界。
李春雨“反弹琵琶”的诗情也很有味道:“我坐在一条河上/垂钓时间//耳朵贴在河面/听不见流水的声音//抛出去的鱼饵/纷纷逃离,奔向鱼”(《垂钓》)。这种意象,既有八大山人“远岫近如见,千山一画中。坐来石上云,乍谓壶中起”的禅意,也有静观世相才能呈现出的种种乖异。
所有这些纵横、沉郁、哲思的文人情愫,无疑是李春雨金石创作别具一格的“天赋”所在。
二
好的艺术作品必然是文而化之的道的弘扬。中国传统艺术都是“我手写我心”,通过渊博的知识,恰当、简明和完美地表达出强烈的个性、心性和心志,如情感、意志、思维、观点和境界等,以此表达出更具有普适性、独创性、共鸣性的闪光灵魂,从而使作品更趋自然、灵性的道。
先不论李春雨那些揭示人性、社会性的小说,单从李春雨已经在《中国书画报》等媒体发表对书法、绘画和篆刻的见识、观点和评论就可以看出,他广闻博识,勤思善辨,对艺术的见解无疑也是他艺术创作知行合一、相互融容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艺术评论必然要探讨技法,但技法一定要契合表达作品内涵的核心,并以此来衬托、展示和凸显作品的精神魅力。春雨评论闻问的篆刻作品,并不简单而具象地描绘其刀工、字构或布白之类,而是运用文学的方法:“观其工稳印如老僧入定,物我两忘,游刃有余;写意印则如将军上马,万夫难敌,挥洒自如。”“边框似圆非圆,似方非方,边线虚虚实实,文字和边框有粘连,亦有虚化而无违和之感,新奇不失古意,率真不失沉厚,雄强而别有温婉,浓烈而平添疏淡,其趣者生焉。”(《抱朴归真 行稳致远——品读闻问篆刻》)……如此种种,混沌而生动、抽象又具象,艺术地给予作品积极而高雅的评价。
李春雨在艺术评论中,还兼具一定的批评性。如他建议篆刻家闻问,“篆刻线条的处理要注重含蓄和浑厚……印面要呈现宁静自然之象。”他建议书法家许强,“在临池和创作当中,注重研读历代书论以求认识上的深化和整体上的把握。”他在篆刻评论中指出,“篆刻作品的个性不但要有(篆刻家)自己的审美情趣和审美印式,也要符合时代的审美。毕竟成功的篆刻作品需要有内涵,需要深刻,需要有人文精神。”
这种高屋建瓴、针砭时弊的批评性意见或建议,既是对同侪作品的评判和激励,也是李春雨自己对篆刻艺术品格追求的显现。

得江山之助
三
李春雨还是一位书法家,比较擅长大篆。
李春雨自幼喜欢书法,学业之余就利用一切空闲时间,遍临真草隶篆,且小有成就,多次在全国及省内书法比赛中获奖。渐长,他对方寸之间可以刻画大千世界的篆刻日益倾心,投入时间精力巨大。但当时,篆刻界依然延续盛行了二十多年的流派印、铁线篆等这些复古主义印风,即“印中求印”。年轻气盛的李春雨显然不愿亦步亦趋,在古贤打造的窠臼里讨生活。他一边刻苦临池,在书法中修炼技法;一边深入思考,从书法中寻求突破篆刻的“天机”,试图“书中求印”。
书法中,最能表情达意的字体无疑是草书。草书解衣盘礴、淋漓肆意的书风是一种格调,是一种品质,更是一种精神。但草书入印也有先天不足:不易辨识,只可偶尔为之。适合制印的书体一般有两种,一是隶书,二是篆书。篆隶书体在书法史不拘一格,各显风骚,神采飞扬。相比较而言,篆书入印更具有优势:历史传承的正统性,大众审美的延续性。这在当时几乎就是醍醐灌顶般的重大发现。悟到这些,李春雨信心倍增,用功更勤,钟鼎吉金、楚晋简牍、汉印封泥等都成了他研习和修炼的重点。
现在欣赏李春雨的大篆书法,可以看出,《散氏盘》《大盂鼎》《石鼓文》等对他的大篆书法有着深刻的影响。
四
搞篆刻,如果没有对上古文字深入的理解、研究和掌握,想真正在篆刻艺术有所成就是不可能的。毋庸置疑,很多人的篆刻,只是喜好,只是为了篆刻而篆刻。他们把一些字帖、字典上的文字照本宣科地复制上印面,图得是好看,像,其实并没有更深更高的追求。这当然也是市场经济大背景下整个艺术圈的通病。但李春雨不同,他是作家,是诗人,是文艺评论家,尤其还是书法家,或者说还是古文字研究专家。这些看似驳杂的身份印记,其实是一种文化情怀,对从事篆刻其实具有非常的价值,在当代艺术圈实属难能可贵。这些厚实广博的文化底蕴,可以说就是他篆刻作品超凡脱俗的保证。
李春雨的篆刻,不论白文朱文,线条古朴沉拔,力能曲铁;圭角方圆互见,刚柔并济;字体欹侧长板,因势利导;布白疏密由心,张弛有度;边框粗细连断,一任自然。
李春雨非常注重文字内容与印面布局的整体协调,如《只争朝夕》的紧凑,《岭上多白云》的空灵,《万岁不败》的朴茂。也如《物外游》整体结构取象近似“心”,颇有“天人合一”之况;《敬事而信》则将“而”游离于一角,其它几个字紧靠在一起,似乎在强调“敬事”才得“信”的哲理;《老子犹龙》的“龙”字,将末端混沌,有如“神龙见首不见尾”。李春雨的篆印边款也颇为用心:魏楷、章草、行书、行草,随性而为,不一而足。
总之,李春雨的篆刻就像他评价其他篆刻家一样,讲究“含蓄之美,中和之致”,讲究“似曾相识”而“莫可名状”,讲究“瑰丽奇肆”的“变易”“印化”,讲究“生机意味”而“气象万千”。他的篆刻,无疑是古朴的,也是新奇的;是人文的,也是自然的;是诗意的,也是物化的;是艺术的,更是“守道”的。他的篆刻作品,往往“善利万物而不争”,仿佛旷野踽踽独行的得道高士,表面收敛,内心随意,拙正,端庄,内涵,大气,却自有一种冲和儒雅的浪漫气象。(曾强)
作者系山西大同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
【责任编辑 陈畅 实习生 翟培辰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