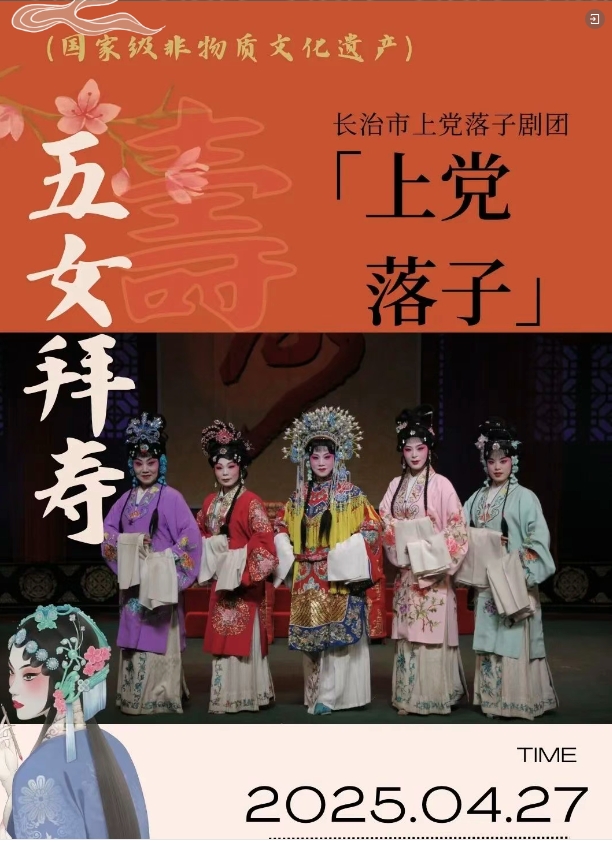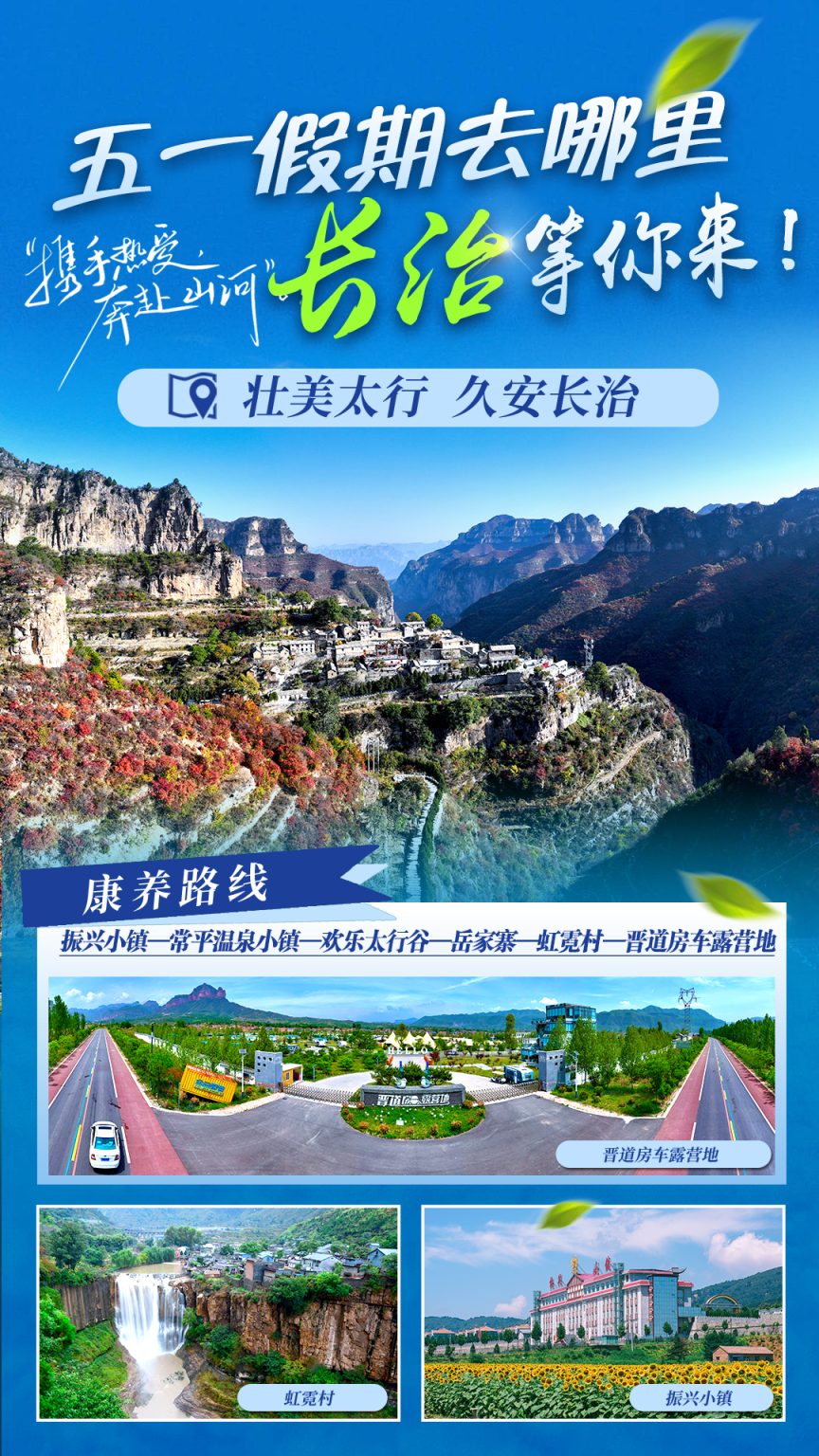过去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一直不大喜欢外国人写的文字,年轻时尤其如此,总觉得老外们不会审美。一段话明明有很多很美的表达方式,却偏偏要直来直去,用最原始的方式,直接了当地怼到读者的脸前。更有甚者,絮絮叨叨,啰哩啰嗦,让人无端地生出几分厌恶来,就比如杰罗姆·大卫·塞林格的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,就是让人厌恶的典型。相对而言,我们汉语的表述就雅致多了——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,多美,看完一遍,就得闭上眼睛再复盘一遍。而外国的文字就没这种境界,进而也就直接了当、以偏概全地得出了一个“外国人没文化”“欧洲依然是黑暗的中世纪”这样的结论来。然而,虚伪的是,就是带着这种根深蒂固的傲慢与偏见,我居然看完了很多的外国文学作品,有名著,也有三流作家们的段子,自己也很矛盾,究竟是审美上的双标还是意识形态的堕落。
导致态度发生根本性改变的,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完了杰克·凯鲁亚克的《达摩流浪者》。依然是文字层面的絮絮叨叨,依然是行文方式上的直来直去,没有风雅颂,更谈不上赋比兴,就是天马行空地讲一段并不很特别的故事。但看完全书,心脏却被狠狠地撞了一下,一扇窗户突然被打开了,有光照了进来,所有种种蒙尘于心底的众物,一时鲜亮了起来。就仿佛是沉睡于太平洋的郑和宝船在新技术的加持下,终于重见天日一样。人居然可以这样生活!文学居然可以这样表达!这种审美层面的顿悟,会带来思维方式的多米诺效应,再回头看曾经读过的外国作品,立刻就显的层次分明了。《百年孤独》之悲劲苍凉、《巴黎圣母院》之悲天怜人、《最后一个莫西干人》之悲愤壮怀、《威尼斯商人》之悲喜交加……总是在用漫长的叙事来铺陈,用间隔的喜剧元素来调剂,最后用厚重的悲的大基调来思考。总得来讲,外国作品更擅长于对传价值观的批判和对人性的思考,就像哈姆雷特的呐喊“To be or not to be”,而中国作品则更加追求“文章本天成,妙手偶得之”那样一种人性与天道的耦合。
最早认识杰克·凯鲁亚克是二十年前了,当时正在看都梁的《血色浪漫》,主人公钟跃民是凯鲁亚克的狂热粉,一心想追求“在路上”的生活状态,甚至于放弃了转业安置的指标,和另外一个不着调的“傻子”高玥异想天开地要搞一个“煎饼果子托拉斯”,进而冲出亚洲,走向世界,他们不止是说说而已,而是真的那么去干了。那种令人窒息的疯狂,也浪漫的让人无法按耐地颤抖。所谓的爱乌及屋不过如此,因为喜欢都梁,所以喜欢血色浪漫,进而喜欢钟跃民,因为喜欢钟跃民,所以喜欢杰克·凯鲁亚克,进而跟着看了小说版和电影版的《在路上》,在那个价值观迷失,普遍自我否定的年代,这样一帮被主流价值观否定的“垮掉的一代”,心怀星辰大海,始终以在路上的姿态,寻找迷雾中的生命真谛,并且永远年轻,永远热泪盈眶。沉浸在这种作品中,总会有一种错觉,似乎在某一瞬间,抓住了那种热泪盈眶的内核,下一个瞬间,却发现自己依然在起点,怯懦地跟着别人一起嘲笑那些行者。
以杰克·凯鲁亚克为起点,我兴起了对“松散结构文学”的深厚兴趣,陆续地看了英国作家约翰逊的《不幸者》,米兰昆德拉的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,毛姆的《月亮与六便士》,逐渐成长为钟跃民式的杰克粉,在当今这个普遍流行“玛丽苏”的时代,我居然是个“杰克粉”,多么的不着调!可是骨子里的不着调一经唤醒,便会愈演愈烈,直至走火入魔。“杰克粉”们最低层次的信仰,大约便是诗和远方了,即使未必真的有放下一切,看看这“big big world”的勇气,但出走的欲望却始终是心头百转千回的执着。这些年,我置办了各种种样户外的行头,全套的爬山装备、全套的钓鱼装备、全套的跑步装备,以及满脑子的四海八荒,于家事国事的夹缝中,也厚着脸皮走过了很多地方,登过了珠峰,穿越过了沙漠,在格尔木发过呆,于布尔津醉过酒,夜宿过荒寺,流浪过丽江……以至于现在年龄渐长、筋骨乏累,窜不动、浪不了的年岁,只能写写文章过过嘴瘾,写的也全是散文!图的就是一个随兴和自由。与其说,是在致敬杰克,还不如说,是在致敬回不去的青春和放不下的柴米油盐。
前几年,播出了一档子音乐综艺节目,《乐队的夏天》,我是喜欢的,还写了很多非专业的乐评。那年,加起来有两百多岁的痛仰乐队复出了,一把年纪的高峰穿着皮夹克牛仔裤,声嘶力竭地唱出陪伴我长大的《西湖》《再见杰克》,唱到兴起处,这个老汉像个年轻人一样跳水、摔吉他、五音不全地呐喊,台下所有没有真正长大的杰克们也跟着五音不全地呐喊……在破音的瞬间,我的心也跟着破防,那个象征青春和热泪的杰克,没有随着时光变迁而与时俱进,永远地停留在了皮夹克和牛仔裤的时代。我们这代人,站在时代的列车上,作别渐行渐远的青春,以及停留在光晕里的杰克,被时间裹挟着,跌跌撞撞地一路向前,假装自己长大了。这一幕在看电视剧《漫长的季节》时,范伟扮演的火车司机告别过去的自己时,被精准诠释,就是这种饱含眼泪但是笑着的告别,让一代人永远地停留在了过去,然后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“往前走,别回头”。
再见,杰克,时间不想等待,我得走了。茫茫然,跟着你走了那么久,一直没有停下来想想,回头时,我已经是最后一个长大的小孩。(徐语)
【责任编辑 陈畅 实习生 翟培辰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