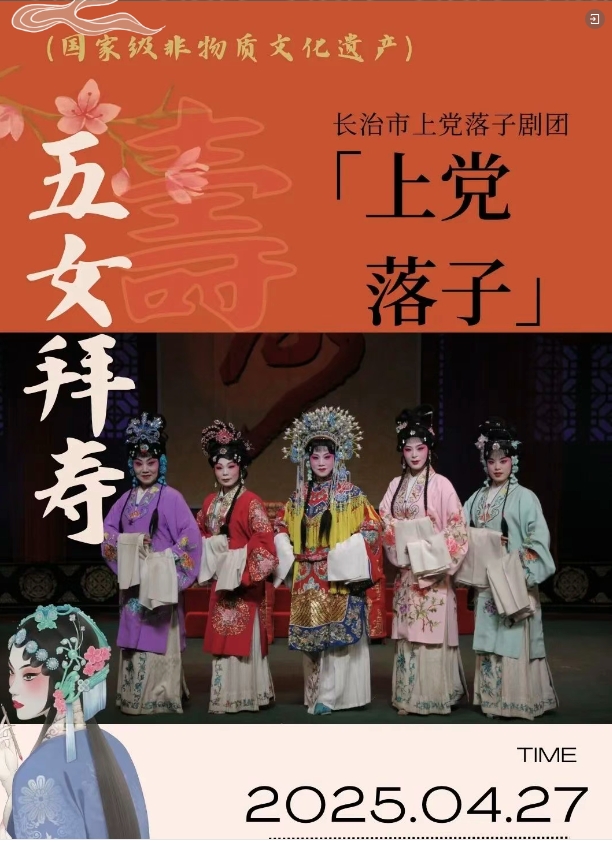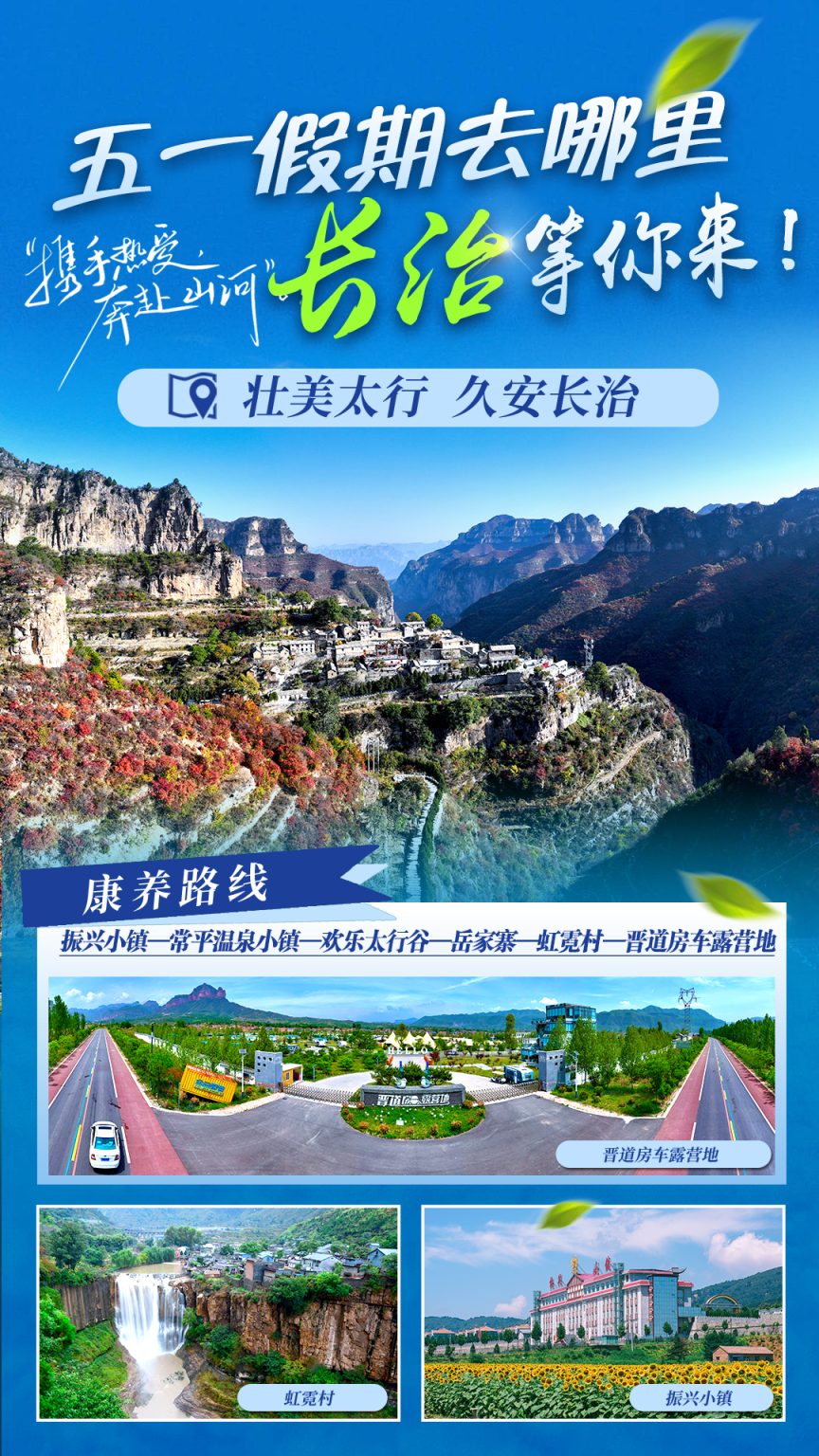诗人,是大地的歌者,他们跋涉原野,他们泛舟河流,他们行吟高歌,他们倚风长啸,他们在梦里草原弹奏冬不拉,也在纸上疆场征战攻伐,他们的漫漫足迹,成了垒筑诗歌巴别之塔的碎石砖瓦与骨骼血肉,也构筑起诗人个体的心灵底色。这种人生轨迹与精神漫旅的跋涉史,在落葵身上有着真切的体现。
一、在高平,他穿上了“孩提时的鞋子”
高平之谓泫氏、长平,乃神农炎帝故里,长平之战遗址,先祖遍尝百草拯救苍生的献身精神,两千多年前回响历史长空的悲怆屠戮,造就了高平人豪爽热心、重情重义的性情与骨子里的悲伤气息。这种精神气质,在高平诗人身上表现突出。从时空角度看,高平诗人又可分为本土和外流诗人两拨。前者,以杨凤楼、申建鹏、王海云等诗人为代表(其中前两位皆英年早逝),成为高平本土诗歌创作的中坚力量。后者,则包括了李杜、悦芳、落葵、牛梦龙、杨秀清等诗人,他们如蒲公英一样散落在省城和晋城。正是这两支队伍,共同构筑起了高平诗歌的厚重与多元。
落葵是高平人,虽然他后来离开了高平,常年在外漂泊,但他灵魂里却流淌着高平地域的血液,他做人认真、虔诚,性情粗犷,感情真挚,这些都与他的故乡高平有着内在的关联。我们常说,一个人无论走多远,都穿着孩提时的鞋子,是有内在依据的,这在落葵身上有着真真切切地体现。落葵擅写亲情,在《父亲的大手》《照壁庄园的孩子》《蓝色火焰》《中秋陪女儿摘苹果》等诗歌中,我们能感受到一种豪爽与细腻相与交织、融为一体的情感质地,这就如同他和他的故乡一样互相依恋、骨肉相连。在诗歌《中秋陪女儿摘苹果》中,落葵这样写道:
在我的怀抱,你用力去扯一个苹果,苹果蒂上细密的绒毛,与你的小手臂相似,去年,你尚未学会走路,我教你抓一片叶子,那时,你还不明白何为果实。
我想,落葵之于高平,是否也如他诗中的小女孩,对这片土地有着孩子一般的亲情依赖、倚靠与灵肉寄托。家乡的一草一木,一山一水,一定构成了他“孩提时的鞋子”。他正是穿着这双鞋子,后来前往祖国的西北边境,开启了他人生的漂泊旅程。
二、新疆给予了他偾张的血脉
新疆7年,使落葵的诗歌真正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境界。新疆是一个大地方,占据了中国国土面积的1/6。这种大,代表着一种空旷与空灵,雄浑与苍茫,能够给予人以大地上的思索。倘若扩展一下,以新疆所代表的西部为观照对象,在新时期数十年的文学脉动中,其无疑承载着中国文学一个浩浩汤汤的宏阔河道,如果没有西部文学,中国的文学注定黯然失色。事实上,整个西北地区,是出大诗人、大作家的地方,王蒙、张贤亮、昌耀、海子、红柯、刘亮程、叶舟等诸多作家都曾居住在西部抑或西进过,面对西部的旷远与浩瀚,确实能够给人带来一种精神层面的冲击力。落葵在新疆的7年,正是他青春年少、意气风发的年龄。正是在这7年中,新疆给与了落葵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,这其中,又表现为一体两翼的两个层面:其一,边地的血性。其二,大地情结。有诗为见:
蒙古族少年骑着马,持鞭望着远方,成片的白云搬运着黑夜,像一首首旅人之歌。——《十月》
宽阔的河面大部分已干涸藏青色的石头,铺满河水冲击的平原那是青史里,勇士与战马的骨头。——《玛纳斯河》
我抬头看见鹰的翅膀我不知怎样回答心里的空旷。——《迷路》
荒凉已无城可守灯盏打着马赛克在眼睛和夜色之中坐下来。——《夜过星星峡》
新疆7年,使得落葵真正融入了西部的浩瀚苍茫之中,也塑造了他诗歌中西部天空下的一腔热血,激扬着西北大地那阔大、粗犷的豪情与张扬的血性。或许正如席勒在《论朴素的诗与感伤的诗》中所阐说的那样,真正朴素的诗只存在于人类童年时代,那种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状态之下。而新疆或曰整个西部,在某种程度上以边缘化的姿态,弥补了东部高度现代文明后物质富足的同时,人性压抑的一面,给予人一方相对可以自由释放性灵的天空。因而当数年后,落葵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西部,便对于这片土地上的山川、河流,逝去的一切满怀依恋,于是有了如是书写:“吃完最后一口馕,舔去最后一颗皮牙子粒/就要说再见了//细细听着,发动机里发出的声音/像是我喉咙里发出的哽咽之声。”但不管怎样,对于一位诗人而言,新疆的经历确实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,激活了他诗人气质中激扬、豪放的一面。
三、他有着近乎虔诚的诗意追求
落葵对于诗歌艺术的追求,近乎虔诚。诗歌,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他现实生活外极为重要的精神构筑。从诗集名字出发,《在沸腾中抽身离开》本身便表明了诗人不甘于喧嚣世俗社会沉沦的决心。在同题诗中,诗人用“在沸水里/谈一条鱼的自由”的决心意志,来表明自己在翻滚如沸水的时代中,保守个体意志的强大内心。这,或许隐含着诗人抗拒浮躁世界的坚定意志。
具体而言,诗人落葵近乎虔诚的诗意追求,集中地表现在两个互为支撑的向度。其一,现世中精神的葆守。其二,诗意中哲学的思索。事实上,我们都是社会的、集体的、秩序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,但诗人给我们带来的却可能是一种更富有个体性的独立人格。这,大抵如同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所宣称的那样,如果他在战争中死去希望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上简单的几个字:“那个个人”。或许,一个真诗人,一生的使命或信条便是永不停歇地探寻着霓虹灯下纷扰人世中,作为独一生命个体的“那一个”。因为,“黑夜,永远是准确退潮后/留给人类的岛屿”(《深夜航班》);因为,我们需要“给一条河奔赴的自由/给一只蚂蚁清澈和澄明”、需要“原谅一封未寄出的信/一瓶跌倒的清酒的悲伤”(《在尘世无尽地奔跑》)。
是啊,我们生活的世界何其荒芜!你看,在《偌大城市,不识一人》中,诗人落葵这样写道:“一百年前,荒沙土道/骆驼驮着炭块,用项下摇铃/摇来黄昏和黑夜”;而一百年后呢?“车来车往/满城尾气像亲人一样/包裹着孤独的人”。这,便是我们存活的一个热闹到沸腾的世界的真实样貌。你,我,他,皆被这一切包裹着、氤氲着、甚至陶醉着、迷恋着。而正是有落葵这样虔诚、执着于艺术世界的诗人的存在,才让我们有了子弹穿透胸部阵痛之后的向死而生的决绝,有了滂沱大雨中孤舟一苇渡江的生命力量。
四、让时间来裁决未来一切
就目前落葵诗集《在沸腾中抽身离开》所呈现的面貌来看,还有一些不尽完美之处,我想从三个层面简要阐说。
第一,结构与逻辑。
结构是一首诗的骨骼,一个好诗人要有严苛的结构意识。比如,冯至曾在1939—1946年西南联大7年时间,创作了个人“精神笔录”的27首十四行诗,并集结而成《十四行集》。这其中,每一首诗都恪守着整一、严谨的结构。而在结构得当基础上,诗歌逻辑的重要性亦不言而喻。因为本质而言,诗歌是句子与句子之间的灵肉连接,如果逻辑松散,赋予其中的冲击力自然会弱,在此,落葵的有些诗歌可能还需要凝练与舒展双向开掘。
第二,意象与意境。
诗歌讲究含蓄蕴藉,蕴藉常凝于点睛之笔,一个好的意象,本身或许就容蓄着好的意境。意象可以是一瞬间的感受,如庞德的《在地铁站》,卞之琳的《断章》;也可以是一个集群,如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、穆旦的《赞美》。具体到山西诗人,譬如张二棍就是构筑意象进而生发意境的高手,在他的诗歌如《恩光》、《在乡下,神是如此朴素》都有着数行之内便让人惊叹的意象体。在落葵身上,我们也确乎看到了他的努力,例如在《花豹》这首诗中,有“我的心系在一只花豹的尾巴上”这样让人眼前一亮的诗句,在《雪下起》中,他的情景交融也做的很有力度。但也存在一些诗歌,意象甚至多种意象的搭配,似乎还有进一步打磨的空间。
第三,一首诗意识。
所谓一首诗意识,就是要力争写出一首让人记得住的精粹的珠玉之作。这,可能是大多数诗人梦寐以求的梦想。大部分诗人终其一生,也没能留下一首诗歌让人铭记,而只与他的“诗人”的名号一起走向速朽。这在当下看似热闹、繁荣诗歌创作中,最典型地表现在风格的辨识度与灵魂的深度的匮乏。无疑,诗歌创作是一个河蚌怀珠、集腋成裘的艰辛过程。落葵作为一位有着虔诚诗歌追求的诗人,相信能以此为警戒。也祝愿诗人落葵,能够精益求精,日益精进,早日写出一流的诗歌作品。
一切的一切,我们留待时间来进行诗意的裁决。(董晓可)
【责任编辑 陈畅 实习生 翟培辰】